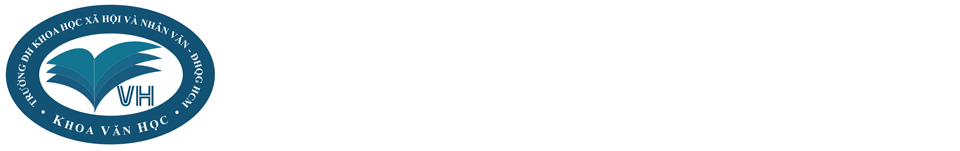1927年冬天,鲁迅这样概括中国的状况:“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2]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从龚自珍、曾国藩那两代人意识到“颓世”难挽、“洋患”逼人,到今天全社会亟亟“与世界接轨”,中国人在被动“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跌跌撞撞了一百五十年。从某些指标——例如GDP和太空探测技术——来看,今日中国已经相当“现代”,但一些更重要方面的状况:社会制度、“人心”、前景想象、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 却表明,中国社会并没有解决“如何现代”——更准确的说法是“何种现代”——的问题。犹如一个在无路之路上艰难跋涉、屡屡迷途的登山者,中国不断地发现自己依然处在不得不“现代”的路程之中,那一座最消耗体力、同时包含了最大希望和最大危险的山口,依然还在前面。但是,从另一面来看,那山口已经不远,社会内部长久积聚的各种深层因素的冲突,这些冲突凸显的整个世界的“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非如此“现代化”就别无他路的大趋势,可世界又难以承受这个“现代化”,开始显露和激化。如果乐观——或者悲观——一点,那就可以说,我们正站在鲁迅所说的这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的末端,甚至已经是开始走进“大时代”了。
中国的“现代文学”,就在这样的进向或开始进入“大时代”的时代里产生,并因此形成其具有世界意义的特点。当然,这里说的世界意义,并不仅指贡献优异的作品,也同样指呈现逼人深思的问题,甚至是提供惨重的教训。
一
中国是一个自然和文化上都堪称巨大的社会。进入十九世纪的时候,它有4亿多的人口,一套不断扩展、差不多延续了五千年、没有被外力完全打破过的文化系统,和一种也是持续了数千年的天下居中、世界中心的观念。正因为是这样一个社会,一旦卷入西洋人推动、因而是以西洋为榜样,已经达到全球规模、因而不可能单独退出的“现代化”运动,它的文化人群中,很自然就会产生如下持续的双重的冲动:
一个是要用西洋——包括苏俄——的模式改造中国,将它转变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以适应新的世界竞争,进而在其中占据一个优越的位置。一百五十年来,这个冲动孕育了无数思想活动和社会实践。单就前者来说,将“西洋”/苏俄奉为样板,再给它竖两根支撑,一根是“普遍人类”,一根是“历史规律”,然后拿样板对比中国的现实,将各种对中国现实和历史的不满,统统转化为“西化”——或“苏维埃化”——中国的实践的激情:身为跨越二十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对这一套思想活动及其各种政治、经济和学术形式,是非常熟悉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另一个是要超越西洋或苏俄,创造比它们更理想的国家和世界。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这“理想”的标准,主要并非搬自西洋或苏俄,而是取自中国本土,或者是新阐释的20世纪之前的传统文化,或者是20世纪新产生的革命文化,尽管这阐释和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正是西洋或俄苏思想的影响。二是这“理想”要覆盖的,并不只是中国,而是整个人类社会,之所以要将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就因为这是迈向建造理想世界的第一步。在十九世纪晚期,这个冲动已经萌发,孕育出一系列先后超越西洋和东洋、最后达到人类——甚至超人类——之大同的大气磅礴的梦想。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间国内国际的动荡和危机,更深刻刺激了这个冲动,令它发展出多种重新解释中国及其他非西方文化和社会传统、企图用它们来救治当世——中国和世界——之弊的思想和学术努力。也是在二十世纪早期,一系列可以用“左翼”统称的、坚决否定现代西洋式的社会结构、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思想和理论活动,开始从另一个侧面表达这一冲动。进入1930年代以后,日益严峻的国内冲突和外国侵略明显压制住了这个冲动的其他表达,左翼[4]思想就成为延续它的一类主要的形式。
这是一个翻天覆地、重造社会的时代,无论怎样的狂想似乎都有实现的可能。至少到1950年代为止,中国文化人大体都还能保持着“立功”的激情,许多人既是狂想者,也是政治家,是有社会影响力的行动者。因此,“超越”的冲动同样孕育了大量的社会实践。从章太炎以《中华民国解》为新国家奠定历史和文化根据,到孙中山以“五权分立”勾勒比西洋更优异的政治制度;从周氏兄弟印《语丝》,尝试破除现代商业对传媒的束缚,到马一浮办复性书院,探究学校体制之外的教育之路;从1920年代初少数青年人学习日本的“新村”运动,在中国提倡类似的试验,到1930年代以后奉苏联为样板,持续不断、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改造:这些意在“超越”的实践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用说,它们的后果至今还以多样的方式,深刻影响着至少是今日的中国人。
综观二十世纪,这“西化”和“超越”冲动的关系始终很复杂,有时候互相激励、甚至因此融汇,有时候却互相冲突、你死我活。这两个冲动的各种具体表达和实践之间,更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缠混淆,错综复杂。即使是最看不上西洋的人,也明白不“西化”就难以“强国”的无情现实,越是想最后超越西洋,反而越要尽早“西化”。倘说康有为式的大同理想,正属于“超越”冲动的第一批表现,它却同时为那“西化”冲动的正当,作了强有力的论证。从晚清到1970年代中期,各种版本的“强国”方案——包括1974年重新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都大体遵循了这一从“超越”的角度肯定并收揽“西化”的思路。另一方面,早在二十世纪初,那些由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领头的“理想小说”,就触目地显示了“超越”冲动内含的士大夫君临天下的古典情怀,1960年代晚期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红卫兵”欢呼“世界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的盛大场面,更令人不能不想起昔日百姓对“天子”的五体投地。正是对此种新衣冠内的旧灵魂的疑惧和反感,不断地驱人转向对西洋的崇拜,浇灭他的“超越”冲动,甚至令他安心于做“美国人”——不仅是“今夜”,也不仅是“我们”。[5]
1918年,陈独秀们抨击传统、倡导西化的声音最响亮的时候,李大钊却呼吁东洋和西洋文明各自反省、调和,创造“第三新文明”。[6]这当然是充分表现了五四时代激进思想内部的多重旋律,甚至是一个旋律内部的多样音调,但反过来说,激进思想的这一李大钊式的“多样”特质,又预示了“超越”冲动在以后的延续中不知不觉被收窄、甚至消溶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前景。1957年,张君劢以“新儒家思想”对抗“不正统的共产主义”,却同时指出,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侵略和文化灭绝,促成了此种“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7]他所以倡导“新儒家”,是为了实现中西方文化的平等和“友善合作”,这似乎体现了“超越”冲动在左翼思想之外的另一种延续,他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后果的洞察,也再次显示了这延续对中国现代思想的正面意义。但是,与当时中国大陆“埋葬美帝国主义”的全民兴奋相比,“超越”冲动在大陆之外的这一路延续,还是更清楚地暴露了这个冲动的想象和实践空间的急剧缩小:五十年前康有为们那一份创造比西洋更文明的新世界的雄心,日渐消退,惟有“保种”、“保教”的焦虑,甚至是“保”而不得的悲观,愈益膨胀。
不知道世界各地其他那些先后被拖入“现代化”历史运动的非西方社会中,是否也有一些和一百五十年来的中国一样,同时被激发起这样分明而强烈的双重冲动。从梁启超开始,许多心存“超越西洋”的志向的知识分子,都特别愿意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地域广阔、人多、历史悠久、文化从未被外力灭绝过…… 这些说法常常显得夸张,令人疑心是自己给自己打鼓,但有一点他们说对了,那就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军队攻进北京的时候,中国士大夫依然普遍相信自己有世界上最文明的文化。从西洋式“现代”的角度看,这当然是闭塞和可笑的自大,但今天回过头来,我们却也应该看到,这“闭塞”和“自大”背后,是有许多别的情况的支撑的:传统的政治和教育制度、根深蒂固的诗书农耕的生活方式、对西洋古典和现代思想的初步了解、对中外数十年“现代化”状况的深切感受…… 其实是这些情况汇合在一起,共同培养了清末民初几代文化人的狂想的底气:不仅仅以被西洋接纳为荣,也不愿只以功利的成败定是非,不甘心接受弱肉强食的新世界法则,总是克制不住地要构想一个更文明的和平世界,一个他们——例如章太炎——不愿意用“现代”命名的世界。当然,这也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和那些企图继续紧闭门窗、固守一隅的专制、颟顸之徒划清了界限,他们是睁了眼看世界的人,想的也是整个的世界,是包括了昔日所谓各色夷狄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华夏的中国。
一百五十年间这两种冲动互相激荡的历史,远非上面讲的几个例子所能代表。我所以不避粗陋地如此概述,只是想说一点:正是这两个冲动的共生和相伴,给了中国人一个珍贵的历史可能,一个形成阔大、深邃、因此也较为丰富的现代意识的可能。主要正是它们之间的复杂的互动,拓展和限定了中国现代意识——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思想——的大致范围和深度,进而促成了它的若干重要的特点。比如说,那种从一开始就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仅是从“中国”去看“世界”——的宽阔的眼光,那种也是从一开始就萌发的改变现存全球秩序——不仅仅是在其中谋一个好位置——的理想和激情。不用说,也正是这些互动的活跃、扩展、深化,或者被压抑、被破坏、奄奄一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中国现代意识的状况:有时候广阔而丰富,有时候——譬如现在——残破而狭窄。
如果还是要用“现代性”这个概念,那就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或者后退一步,是否可能——“超越西洋”。重复一句, “超越”的意思是使整个世界更文明,而不是让中国比西洋更西洋。人的历史应该是不断使自己更“好”——我借用“文明”一词来描述这个“好”——的历史,它不能因为现代西洋的出现而终结。
二
中国的现代文学,正是和这样的双重冲动一起诞生的。一百五十年间,文学经常是这些冲动的最重要的表达者,它以文字赋予它们生动的故事和意象形式,引发读者情感的共鸣,从而最大规模地传播和激发这些冲动。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赋形”的过程中,文学大大扩展了这些冲动的内涵,不但使它们变得具体,而且使它们因这具体而变得丰富。因此,在很多时候,文学又成了这些冲动的最重要的发展者。当人们将这些冲动付诸实践、因而势必从不同的角度将其简化、抽象,甚至将它们显现、凝固为标签式的概念和制度的时候,文学却常在精神和心理的领域里反向而行,在这些冲动的内部和周围,为它们开辟许多新的难以抽象的内容。
举一个例子:直到今天,许多读者一看见“阿Q”,依然会习惯性地想起“精神胜利法”、“民族劣根性”、“改造国民灵魂”等等词汇;一谈到“幻灯片事件”,脑子里也立刻会涌上“麻木”、“弃医从文”、“救治人心”这样的判断。之所以普遍发生这样的联想,当然有学校教育、文学阐释等多方面的原因,但鲁迅创造的这两个意象的文学意味,它们在表达和传播启蒙意识——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候,启蒙都是被解释为“西化”冲动的产物的——时的诗性的适应力,却是整个事情的基础。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不间断地创造这样的人物、故事和意象:凤凰涅磐、高家大院、子夜、陈白露、刘世吾、梁生宝、伤痕、乔厂长上任、李向南、丙崽[8]…… 即便其中有许多很快被人遗忘了,但在各自的脍炙人口的一时间,它们都充分发挥了呈现和促成那双重冲动——特别是其中的“西化”冲动——的巨大作用。
不只是人物、故事和意象,也不只是激发人对这些冲动的共鸣,文学还以多样的方式,参与了对更深一层的精神土壤的翻耕。中国人不再对着皇上磕头了,同时也不再能傲视夷狄了,现在是要做“国民”、要成为“个人”、要当革命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然后又是要找回“自我”了。另一方面,“朝廷”不再能令人安心归属,是“国家”、“民族”、“人类”、“共产主义”、“现代化”、“美国人的生活”轮番出场,来收聚人的认同之心了。在这中国人的头脑不断被重新“格式化”的过程中,文学一直是积极的介入者:第一人称叙事之于“个人”的确立,“乡土文学”之于现代知识视野中的农村想象的形成,杨朔式抒情笔法之于“新中国”青年人情感结构的倾斜,王朔式“佯痞”语调之于“后革命”时代利益至上心态的急速膨胀…… 从某一个角度看,正是人的意识“根部”的这些变化,决定了前述双重冲动的起伏兴衰,而深深锲入这些变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对那些冲动的影响也就更内在,更深远。
应该进一步列出这样一些文学的形象:孔乙己、魏连殳、雨巷、边城、鱼钓、棋王、“命若琴弦”的盲琴师、“小村人”[9]…… 它们在你心中唤起各不相同的情感,引你浸入一些特别而强烈的意趣和氛围,你的感动是如此形形色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不鼓励你亲近“全盘西化”一类的主张。它们更像是体现了文学对那“超越西洋”的冲动的参与,不仅有力地呈现它,更以一系列动人的意境,在中国人心中培养各种非“西化”的情感和趣味,潜移默化。如果更仔细地体会,你又会觉得,它们并不只是将你引向某一种集体的冲动,无论那是否意在“超越”。它们中有一些甚至是要告诉你,这一切都不是关键所在,人生中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文学优长于现代精神生活的其他形式的地方了。它总是自相矛盾,甚至醉心于暧昧和游移。因此,在现代中国,它虽然奋力迎向时代的中心问题,不可避免地深陷那双重冲动的漩涡之中,却又同时从别处——日常生活经验、作家的个性和天赋才能、过去遗留和新产生的非主流文化,等等——获得另外的滋养,不断从漩涡中向外突破,创造出大量既与那些冲动相关、又远非其能包容、往往与之差别、乃至明确冲突的经验和想象。有对那些冲动的绝望,也有对它们的否定,有对那些冲动的义无返顾的逃离,也有向它们的同样坚决的返回…… 正是在与那些冲动的既亲近——以致血肉相连——又疏远——总是心生二意——的深刻纠缠中,现代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质。
这里也举一个例子: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文学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现代专制制度。这制度有极大的弹性,可以是一党专政,也可以是政治、经济寡头的联合集权,可以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市场,也可以是政府控制下的无序市场,可以反资本主义,也可以和资本主义结盟。越是左翼和“革命”色彩浓烈——或曾经浓烈——的政府,控制文学的欲望和能力还越强。正是凭这多变而不离其宗的特点,专制制度不断地强化文学与那双重冲动的关系:因为憎恶政府的管制,便亲近西洋式的“个人”,投身“自由”的市场,因为受不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就转向激进的“革命”,憧憬“人民”的解放…… 从这里,你正可以看到那双重冲动对文学的一种最强劲的吸引,或者说,文学对那些冲动的最惨烈的承担。严酷的制度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最大后果,就是人的心灵的普遍的“病态”——我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姑且用它,而这正是文学处理的主要对象,尤其当任何作家都不可能避免被它感染的时候。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在它与这制度的交往中最终形成,可以说无一例外。
我特别要说一下这些特质中虽有负面意味、却不能单用负面一词概括的部分,它们都和鲁迅说的“大时代”——或者“进向大时代的时代”——直接相关。以那双重冲动为核心发展起来的现代意识,总体上是一种积极的意识:求变,求新,求成功。但是,它却遇上了屡屡迷失方向、千辛万苦攀上山顶却不断发现前面是断崖、时间越来越晚危险也越来越大这种种令人沮丧的境况。迫切求成,却总是不成:这可说是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基本的精神境遇。
有时候,文学似乎并不注意这一点,因此就有了那些热烈鼓吹、欢呼、赞叹的作品。但整个来看,与现代中国人精神活动的其他形式相比,文学还是最敏锐地呈现了对这种境遇的体会。正是从这个体会出发,它才形成了如下这样的特质:
一是各种深具中国特色的“消极”情致的表达:悲观、绝望、虚妄、感伤、自恋、玩世、枯寂…… 这“消极”并不仅在这些情致的内涵,也同样在其表达:它是固执的,却每每又是半遮脸庞、不愿意全露出来的;
一是怎么也不能断根的干预现实的救世的热忱,它不但驱引作家向社会现实搜取创作的素材,而且激励他们创造与之相适的新的艺术形式,甚至不惜重新定义什么是文学;
一是往正面应对社会和时代压力之外的其他方向,开拓确证人生意义和诗意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这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但惟其如此,这些远近不等的开拓,反可能促成对若干混合着相反因素的精神境界的深入的体会:“轻”与“重”、“琐碎”与“巨大”、“通脱”与“隐痛”、“淡漠”与“关切”……
这些特质时断时续地贯穿了到目前为止的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在还没有走出这个“大时代”之前,它们大概还将继续存在。
三
“走向世界文学”,是1980年代大多数作家和研究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判断。现在的认识自然是较为准确了:不是“走向”,而是被迫加入,加入的也不是“世界文学”,而是西洋规划的“世界”:正是这样的“加入”创造了中国的“现代文学”。也就是说,事情主要不是发生在文学层面,而是发生在社会和一般意识层面,那“世界”也并非标准,更非归依之地,它仅仅只是原因。如果这样来看,真正的并非由世界之某一部分规划的“世界文学”,目前就还是远未完成的事物,中国文学的走向其中、融入其中、成为它的一部分,也因此还只是一个可能,或者——乐观一点罢,一个才开始不久、注定会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正因为一切远未结束,中国的现代文学反而获得了作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的可能。不仅是提供关于自身的“寓言”,也不仅是以“病态”启示负面意义上的“问题”,中国文学同时还呈现了探究现代人类和人生困境及其诗意的多种可能,其中有大量今人不易体会的艰辛和惨败,但也分明还有别样的堪称丰富的收获。当然,这收获一定是超出了狭义的文学的范围的。
说到“收获”,就要稍微多说几句。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西洋规划的世界,是一个高度分工的世界,这分工不但是经济和政治的,也是文化和思想的。少数“大国”的人思考全球的、普遍的、抽象的、超越的、乌托邦的、形而上学的、审美的……事,其他“小国”的人专想本地的、具体的、切身的、功利的……事,就是这文化分工的一例。当然,这“大国”之大和“小国”之小,都主要不是看领土、人口、历史和文化,而是看你在全球等级秩序里的位置:五千万人的法国,就比两亿人的印度尼西亚“大”,三亿多人的美国,更是比十四亿人的中国“大”。一旦分工的时间长了,再看见贫弱地区的文化人表达对世界和普遍问题的看法,就不但“大国”的学者不以为意,他自己的同胞也觉得荒唐:你还想这些?想也是空想!庆幸的是,这样的轻视和自我抹杀并不符合现代世界的历史,不符合各地人民的保存下来的记忆。就以中国来说,与那双重冲动一路纠缠着走过来的文学,贡献出了多少对于人生和世界的、并不仅仅属于中国人的体会和想象!这绝不是说中国的现代文学已经如何伟大,相反,在许多时候,这文学的表现是相当糟糕的。但是,惟其在一个愈益深刻地“西化”[10]人类情感的世界上,也惟其常常丧失自我表达的可能和心力,我们反而要特别珍视中国现代文学抵抗情感“西化”的一面,珍视这拒不接受世界的文化分工、挣扎着保持丰富的“空想”志趣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想剥用章太炎当年“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史,先灭其文”的名言,说:欲灭其人,先灭其文学,欲灭其文学,先灭其空想之志趣。
当全世界都开始意识到,面对愈益复杂、变化叵测的现代生存状况,人类不能只有一种西洋式的感觉和思维,当我们终于明白,真正的“世界文学”是必须要和真正的“世界意识”一同生长才可能形成,那么,静下心来体味、发现、重新描述和阐释,不但使我们真正拥有中国现代文学的收获,也让别地的人能较确切地知道这些收获,就是我们今天迫切该做的事了。
2006年7月 上海
[1] 这里的“现代文学”一词中的“现代”,并非一个时间概念,指譬如从1917年到1949年的这一段时期,而是一个有关“意义”或“性质”的概念,指与“是否现代”、“如何现代”或“何种现代”这样的社会问题一同产生并与其相互影响的文学。因此,本文所说的“现代文学”从晚清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很可能——还将延续很长时间。
[2]鲁迅:《〈尘影〉题辞》,《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07页。
[3]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33页。
[4] 本文这里及其后的“左翼”一词,都是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用的,并不仅指中国共产党所组织和领导的思想和实践活动。
[5] 这里借用了2001年“9·11”事件当晚中国一批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化人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声明的标题:《今夜,我们是美国人》。
[6]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北京,《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7] 张君勱:《<新儒家思想史>前言》,《张君勱集》,黄克剑、吴小龙编,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12月版,93页。
[8] 这里列出的“人物、故事和意象”依次取自郭沫若的诗集《女神》(1921)、巴金的长篇小说《家》(1931)、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1933)、曹禺的剧本《日出》(1936)、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6)、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1959)、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1979)、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1984)和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1985)。
[9] 这里列出的“文学形象”依次取自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1919)和《孤独者》(1926)、戴忘舒的诗集《我底记忆》(1929)、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1934)、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鱼钓》(1981)、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1984)、史铁生的短篇小说《命若琴弦》(1985)和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1993)。
[10] 可能这是一个多余的解释:这里说的“‘西化’人类情感”是指在按照现代西洋的模式改造世界各地的人的日常生活——同时通过教育等等的方式传播西洋的现代思想观念、造成各地人民均自觉不自觉地依据这些思想观念来理解自己的感受——的基础上,潜移默化地造成的情感的相类化。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拒绝“自由”、“民主”这样的所谓外来的观念。当然,更进一步说,对不平等的不满和对解放的欲求,是各地人民共有的悠久的传统,并不能仅仅归之于现代西洋。